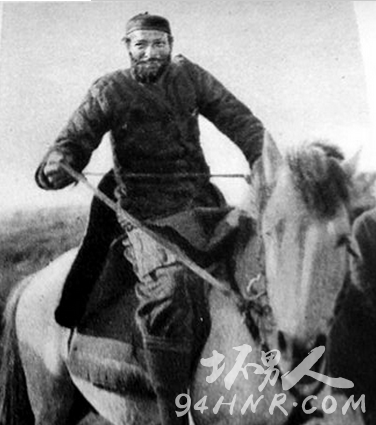80年前,曾有两位西方传教士分别与我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亲身接触相处过,一位是英国人P·A·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另一位是西班牙人西布里亚诺·布拉阿。在和红军接触相处之后,他们分别记述了自己对红军队伍的印象感受。
薄复礼,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1923年春被教会派往我国贵州遵义的教堂任教士,开始其在我国的传教生涯。1934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不久之后的10月1日,薄复礼等人同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这支部队不期而遇,红军扣留了他。对于为什么要扣留薄复礼,肖克将军后来回忆说:“我们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员日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从此,薄复礼跟随红六军团一起历经了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境内,在外宿营达300多处。开始,薄复礼对于红军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 随着时间推移,薄复礼的印象开始改变,部队指战员对他的称呼也渐渐改变,由起初叫他“大鼻子”、“洋鬼子”,后来叫他“薄牧师”,最后叫他“老薄”。直到1936年4月,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军团领导决定让薄复礼离开部队,军团长肖克亲自设宴饯行,专门为薄复礼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临走时,红军还赠送薄复礼10块大洋路费。
一年多时间的朝夕相处,红军给薄复礼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尽量照顾薄复礼的外国习惯和习俗,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他在和红军分别后不久后写的《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一书中回忆说:“行军途中鞋破了,有战士从脚上脱下来给我穿;住宿时总是让我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地板上,而同我一起的士兵们,则全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红军还特地给我配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我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我购买鸡鸭鱼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炼乳罐头等食物。”尤其是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高级将领则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薄复礼写道,红军所到之处, 都要大写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等等。
每到一地,不管停留多久,差不多每个单位都要选择一间较大的房子作“列宁室”,作为学习场所。即便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他们也会自己动手因地制宜建造一间。红军的政治教育更是经常不断。部队宿营后,常召开一些会议,讨论问题,围绕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议题,大家各抒己见,最后由排长进行总结。部队在行军中,首长们先要讲话,呼口号。途中,随处可见个别谈话情景。对新入伍的战士,下的功夫还要多。尽管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红军队伍情绪却十分高昂,常有歌声相伴,歌词种类很多,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有《国际歌》,甚至还有提倡讲卫生的歌。而令他大为惊讶的是,红军队伍中没有人赌博、没有人抽鸦片。红军严明的纪律令他由衷钦佩。
如果说薄复礼对红军由印象不好而到由衷钦佩,另一位西班牙驻福建沙县传教士西布里亚诺·布拉阿也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布拉阿是于1934年1月25日在沙县县城被红军捉住的。这天早晨,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的红军三军团第四师和第六师消灭闽西地方军阀、国民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攻克沙县县城,布拉阿被俘,后于3月初被送到红色首都瑞金。然而,就在短短的时间内,布拉阿由因为听到不少关于红军的谣言而畏惧,变成了在红军队伍中很安心,彻底改变了对红军的印象。布拉阿在被送到瑞金国家保卫局后,于3月3日用西班牙文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34年3月8日《红色中华》第159期第4版上,叙述了他被俘经过和对红军队伍的印象。全文如下: